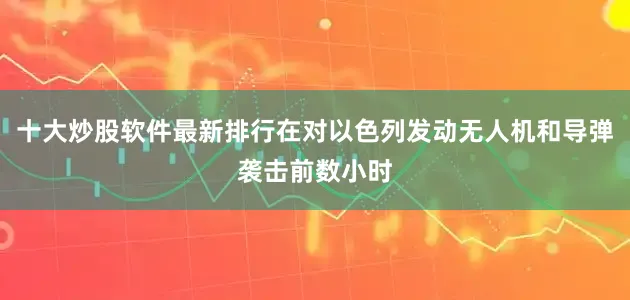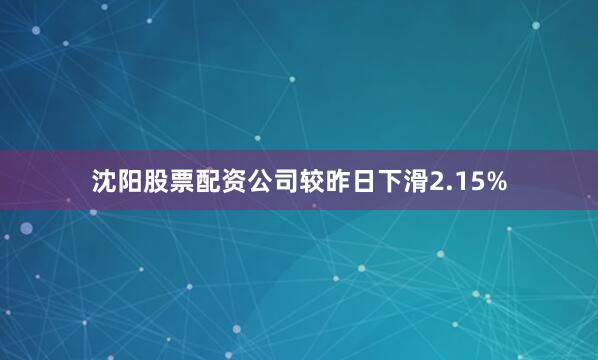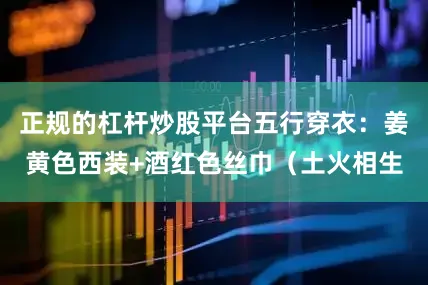日期:2025-08-14 13:07:00

清朝初年,世道初定,却也百废待兴。北方乡间多有流离之人,能安稳度日已是幸事,若想靠着读书谋个前程,更是难如登天。那些掌管科举的官员,眼里只认得世家子弟的名帖,乡野间的才俊,纵有满腹经纶,也常因无钱打点而被挡在考场之外,徒留一声长叹。
在山东滨州的林家庄,有个叫林守拙的汉子。他父亲林老实,原是个本分的木匠,手艺精湛,却因性子耿直,不肯给县丞送礼,被强派了看管黄河堤坝的差事。那堤坝常年失修,一到汛期便险情不断,林老实每次都拼着命去抢险,可稍有差池,就会被役卒按在地上打板子,背上的旧伤叠新伤,到了阴雨天便疼得直不起腰。守拙打小就跟着父亲在堤坝上打转,手里攥着父亲削的木剑,眼里却盯着路过书生掉落的残卷。他不认字,就缠着识字的货郎一句句教,晚上借着月光在沙地上划拉,竟也慢慢读懂了些文章。
有一回,黄河上游下了暴雨,堤坝一处出现管涌,林老实带着几个民夫日夜抢修,还是没堵住。县太爷闻讯赶来,不由分说就命人把林老实按在泥地里打。守拙当时正在附近割草,听见父亲的惨叫声,扔下镰刀就冲了过去,扑在父亲身上,硬生生挨了二十多板子。板子落在背上,像火烧一样疼,他咬着牙不吭声,直到县太爷骂骂咧咧地走了,才扶着父亲回家。晚上趴在炕上,背上的血浸透了褥子,他却还在念叨货郎教的《论语》,母亲在一旁抹泪,他反倒笑着说:“娘,书上说‘士不可以不弘毅’,这点疼算啥。”
展开剩余92%守拙十六岁那年,林老实又被派去给县衙修缮粮仓。粮仓年久失修,梁木朽坏,夜里突然塌了一角,压坏了不少粮食。县丞早就看林老实不顺眼,当即把他锁进大牢,说要问个 “监守自盗” 的罪名。守拙得知消息,揣着家里仅有的半袋小米,连夜赶往县城。他在县衙门口跪了整整一夜,天亮时,县丞出来倒夜壶,见他跪在那里,衣裳都被露水打透了,不耐烦地踢了他一脚:“哪来的叫花子,滚远点!”
守拙抬起头,脸上沾着泥,眼神却亮得很:“大人,我是林老实的儿子林守拙。粮仓倒塌是梁木朽坏,与我爹无关,要罚就罚我吧。”
县丞上下打量他一番,见他虽穿着粗布衣裳,却不像一般庄稼汉那样畏畏缩缩,便冷笑一声:“你倒有孝心。可你知道损坏官粮是什么罪?轻则杖责,重则流放!”
“我愿代父受罚。” 守拙挺直腰板,“只是我爹年事已高,禁不起折腾,求大人开恩。”
恰巧此时,新到任的知县路过,听见这话,停下脚步问:“你这后生,倒有几分骨气。你识字吗?”
守拙答:“略识几个。”
知县便让人取来纸笔,写下 “修仓防患” 四字,让他对个下联。守拙略一思索,提笔写下 “守坝安澜”。知县见他字迹虽稚嫩,却有股刚劲,又问:“你可知这两句话的意思?”
守拙道:“修粮仓是为了防备饥荒,守堤坝是为了安定水患,都是为百姓着想。我爹修仓时就说,梁木要选结实的,地基要打牢固的,不然早晚出事。可县丞大人只催着赶工期,不肯拨银子换木料……”
县丞在一旁听着,脸都白了,慌忙打断他:“你胡说八道什么!”
知县却摆了摆手,盯着守拙道:“你说的是实话?”
守拙从怀里掏出一块朽木:“这是我爹从粮仓梁上拆下来的,里面都生了虫。大人若不信,可去查验。”
知县当即让人去粮仓查看,果然如守拙所说。他勃然大怒,罢免了县丞的职务,又亲自给林老实松了绑,对守拙道:“你不仅孝顺,还明事理。我看你是块读书的料,不如去参加童生试吧,我给你写封推荐信。”
守拙却摇了摇头,给知县磕了个头:“谢大人美意,只是我爹还等着我回家,家里的田也不能荒了。读书是为了明白道理,不是为了做官。若为了功名忘了本分,读再多书也没用。”
知县愣了愣,随即叹了口气:“好一个‘守拙’,果然人如其名。也罢,你既不愿应试,我便免去你爹的差事,再赏你些木料,让他重操旧业吧。”
林老实回家后,对着守拙哭了一场:“是爹没本事,让你受委屈了。”
守拙笑着给父亲擦眼泪:“爹,您教我做人要本分,这比啥都强。再说,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,白天跟着您做木匠活,晚上读读书,日子踏实。”
守拙十八岁那年,娶了邻村的王氏。王氏是个勤快姑娘,梳着两条粗辫子,手上磨出了茧子,却总爱笑。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,还常常帮着林老实拉锯、刨木,守拙在外做活晚了,她就提着灯笼去村口等,灯笼上糊着她亲手剪的 “囍” 字,在黑夜里亮得暖心。
婚后第三年,守拙靠着一手好木匠活,攒了些钱,在镇上开了家木工作坊。他做的家具用料实在,样式也新颖,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来光顾,日子渐渐红火起来。只是王氏的肚子一直没动静,守拙嘴上不说,心里却有些急,夜里读书时,常常对着《诗经》里 “宜尔子孙” 的句子发呆。
镇上有个秀才叫赵敬文,家里颇有资产,却总爱附庸风雅,在自家花园里建了个 “听雨轩”,天天邀请些文人墨客来饮酒赋诗。他听说守拙识字,还会对对联,便让人送来请柬。守拙本不想去,林老实劝他:“去吧,多认识些人总好。再说,人家是秀才,咱别驳了面子。”
守拙拗不过父亲,便去了。那赵敬文长着一副尖脸,说话时总爱眯着眼,见了守拙,皮笑肉不笑地说:“林师傅来了,快请坐。今日我们要以‘雨’为题作诗,林师傅也来一首?”
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,显然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守拙也不恼,端起茶杯喝了一口:“我不会作诗,只会说句大实话。这雨啊,下在田里能浇地,下在屋里要漏雨。建这轩子若只图好看,不把屋顶盖严实了,怕是雨一来,就得忙着搬桌子了。”
众人听了,笑得更欢了。赵敬文的脸却沉了下来:“林师傅这话就俗了。我辈读书人,讲究的是意境,岂是你这匠人能懂的?”
守拙放下茶杯,站起身:“赵先生这话我不敢苟同。不管是读书还是做木匠,都得实在。读书不务实,便是空谈;做活不扎实,便是糊弄。您说这‘听雨轩’有意境,可我看着这梁上的榫卯都没对齐,怕是用不了几年就得散架。”
赵敬文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:“你一个泥腿子,也敢妄议斯文!”
守拙也不争辩,拱了拱手:“打扰各位雅兴了,我告辞。” 说罢,转身就走。出门时,听见赵敬文在后面骂:“真是个榆木疙瘩,难怪叫守拙!”
守拙没回头,心里却想:榆木疙瘩咋了?榆木结实,能顶事。
那天晚上,守拙从镇上回家,走在半路,忽然听见路边的草丛里有响动。他提着灯笼过去一看,是一只黄鼠狼,被猎人设的夹子夹住了腿,血顺着毛流下来,眼里满是惊恐。见守拙过来,它竟像是通人性似的,对着他作揖。
守拙心一软,蹲下身想把夹子撬开,可那夹子太紧,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开。黄鼠狼一瘸一拐地跑了几步,又回过头看了他一眼,然后钻进了树林里。
守拙回到家,刚把灯笼挂好,就听见院子里有动静。他走出去一看,只见一个穿着黄衣的少年站在月光下,眉清目秀,就是脸色有些苍白。那少年见了守拙,纳头便拜:“多谢恩公相救,小的黄九郎,日后必当报答。”
守拙吃了一惊,随即想起那只黄鼠狼,便问:“你是……”
黄九郎笑了笑:“恩公不必惊慌,我虽是异类,却不会害人。我在这山里修行了五十年,今晚本是要渡劫,却不慎落入猎人陷阱,若非恩公相救,恐怕就没命了。”
守拙见他谈吐文雅,不像歹人,便请他进屋坐下,又让王氏端来些点心。黄九郎说起山里的事,什么狐狸如何拜月,松鼠如何藏粮,听得守拙夫妇啧啧称奇。
自此以后,黄九郎常常来拜访,有时送些山里的野果,有时帮着守拙出些木匠活的点子。他设计的一款 “百子柜”,抽屉层层叠叠,既省地方又能装东西,卖得极好。林老实也很喜欢他,常说:“这九郎,比有些读书人还懂事。”
转眼到了林老实六十大寿,守拙想简单办几桌酒席,请些亲戚邻里。黄九郎却道:“林伯操劳一生,该好好热闹热闹。这事交给我,保准让您满意。”
寿宴前一天,黄九郎不知从哪里弄来许多东西。院子里挂满了五彩的灯笼,都是用山里的彩纸糊的,上面画着松鹤延年的图案;堂屋里摆着十几盆菊花,红的、黄的、白的,开得正艳;厨房里更是堆满了食材,有山里的野兔、河里的鲜鱼,还有一坛坛好酒。守拙又惊又喜,问他从哪里弄来的,黄九郎只笑说是朋友送的。
寿宴当天,亲戚邻里都来了,个个赞不绝口。赵敬文也来了,他见院子里布置得雅致,不由有些惊讶,待看到那 “百子柜”,更是眼睛一亮,对守拙道:“林师傅好手艺,这柜子卖不卖?我出双倍价钱。”
守拙还没答话,黄九郎在一旁笑道:“这柜子是林伯的寿礼,不卖。不过赵先生若想要,我可以让守拙哥给您做一个,只是工钱得加倍,毕竟赵先生不差钱。”
赵敬文的脸僵了一下,讪讪地说:“玩笑,玩笑。”
酒过三巡,赵敬文喝多了,开始吹嘘自己的学问,说要给林老实题字。守拙不想扫他的兴,便取来纸笔。赵敬文大笔一挥,写下 “木德长存” 四个大字,又在旁边题了一行小字:“赠木匠林老实”。众人看了,都觉得这题字虽不算上乘,却也贴切。守拙正要道谢,黄九郎却指着那行小字笑道:“赵先生这字,怕是写错了。林伯虽是木匠,却也是读过书、明事理的人,怎能只写‘木匠’二字?不如改成‘大匠’,既显尊重,也合林伯的身份。”
众人听了,都点头称是。赵敬文脸上挂不住,却又不好发作,只得悻悻地改了。
寿宴过后,守拙对黄九郎说:“你今天那样说,怕是得罪赵秀才了。”
黄九郎道:“这种人,就该杀杀他的傲气。他以为读书人就高人一等,其实心里比谁都俗气。”
没过多久,赵敬文家的 “听雨轩” 真的塌了,还砸伤了一个客人。赵敬文怀疑是守拙搞的鬼,跑到作坊里大吵大闹。守拙正忙着干活,头也不抬地说:“我早就说过,那轩子的梁没安好。你若信我,当初让我修修,也不会出这事。”
赵敬文气冲冲地走了,没过几天,就传出他被人告了,说他克扣家仆的月钱,还强占了邻居的地。原来,那些被他欺负过的人,见他失了势,都跑来揭发他。赵敬文被革了秀才功名,还赔了不少钱,从此一蹶不振。
守拙听说后,叹了口气:“其实也不必如此。”
黄九郎道:“这都是他自己做的孽,怪不得别人。只是我用了些小法术,让那些被他欺负的人有胆子站出来罢了。”
守拙有些担心:“你这样做,会不会惹上麻烦?”
黄九郎笑了笑:“放心,我有分寸。”
可没过多久,黄九郎就出事了。那天他来找守拙,脸色惨白,嘴角还带着血,一进门就倒在地上。守拙赶紧把他扶起来,问他怎么了。黄九郎喘着气说:“我用术法帮了那些人,触犯了天条,被师父罚了。他收了我的修为,还打断了我的腿……”
守拙看着他血肉模糊的腿,心里又急又疼,赶紧让王氏找来草药给他敷上。黄九郎道:“我怕是不能再留在这儿了。只是有件事,我得告诉你。明年春天,这里会闹旱灾,你要提前储备些粮食和水,再打几口深井,或许能救不少人。”
守拙点头:“我记住了。你好好养伤,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”
黄九郎摇了摇头:“我的修为没了,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我在山里藏了些银子,你拿去买粮食吧。” 他说了个地址,又从怀里掏出一张药方,“这是治热病的方子,明年旱灾时,定会用上。”
说完,黄九郎就闭上了眼睛,身体渐渐变成了一只黄鼠狼。守拙夫妇大哭了一场,把它埋在了后山的松树下。
第二年春天,果然大旱,河流干涸,田地龟裂。守拙按照黄九郎的嘱咐,开仓放粮,又让人按药方配药,免费发给乡亲们。靠着那些深井和储备的水,村里人都挺了过来,附近村子的人也纷纷来投奔,守拙的作坊成了临时的救济点。
旱灾过后,守拙的名声传开了,都说他是活菩萨。可他心里却空落落的,常常想起黄九郎。王氏见他闷闷不乐,劝他:“九郎是个好妖,老天爷会保佑他的。”
也许是黄九郎在天有灵,那年秋天,王氏竟怀上了。守拙高兴得几夜没合眼,天天给王氏炖鸡汤,走路都怕碰着她。
怀胎十月,王氏生下一个儿子,眉眼竟有几分像黄九郎,尤其是那双眼睛,亮得像山里的星星。守拙给儿子取名叫 “思远”,小名 “九儿”。
九儿长到三岁,就显出了过人的聪慧,教他认字,一遍就记住了,还常常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些奇怪的话,什么 “那是太白金星在值班”,什么 “月亮上的兔子在捣药”。守拙知道,这孩子不一般。
有一天,一个穿着灰袍的道士来到作坊前,说要见守拙。守拙出来一看,那道士仙风道骨,手里拿着一个黄布包。道士笑道:“我是黄九郎的师父,特来送样东西。”
他打开黄布包,里面是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,散发着淡淡的金光。“这是九郎的内丹,他临终前求我,若有来世,让我把这个交给他。如今他托生在你家,这珠子也该物归原主了。”
守拙接过珠子,心里一阵激动:“九郎他……”
道士道:“他尘缘未了,托生为你的儿子,也是天意。这珠子能保他平安长大,只是你要记住,莫让他沾染太多俗事,否则会影响他的修行。”
说罢,道士摸了摸九儿的头:“好孩子,好好跟着你爹娘,将来做个有用的人。” 九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伸手去抓那颗珠子,道士笑了笑,转身就走,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
守拙把珠子给九儿戴上,那珠子一碰到九儿的皮肤,就化作一道金光,钻进了他的身体里。九儿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,指着后山说:“黄哥哥在那里看着我们呢。”
守拙抬头望去,只见后山的松树下,仿佛有个黄衣少年的身影,对着他们挥了挥手,然后渐渐消失在云雾里。
后来,九儿长大了,果然聪明绝顶,十五岁就考中了秀才,可他却对功名不感兴趣,反而跟着守拙学起了木匠活。他做的木器,不仅结实耐用,还透着一股灵气,有人说,他做的椅子,坐上去能让人心情舒畅;他做的床,能让人一夜好眠。
赵敬文后来穷困潦倒,常常来作坊门口徘徊,守拙见他可怜,便时常让王氏给些米粮。赵敬文每次接过米袋,都低着头红着脸,话也说不囫囵。有一回九儿撞见了,指着他背上说:“爹爹,这人后颈有团黑气,怕是心里积了太多愧悔。” 守拙喝止他:“不可胡说。” 赵敬文却猛地跪在地上,对着九儿磕起头来:“小神仙明鉴,我知道错了,真知道错了……”
九儿从那以后,常跑到后山松树下坐着,有时一看就是大半天。守拙悄悄跟过去,见他对着空气说话,时而蹙眉时而笑,问他在跟谁聊天,他总说:“黄哥哥在讲山里的事呢。”
这年冬天来得早,黄河又结了冰,冰面裂开的缝隙能塞进拳头。有天夜里,守拙梦见黄九郎浑身是水地站在床边,急道:“堤坝要塌了,快让乡亲们搬到高处去!” 他惊醒时冷汗涔涔,连夜敲锣召集村民。众人半信半疑,可看守拙说得恳切,还是抱着被褥往村后的土坡挪。天快亮时,只听轰隆一声巨响,黄河冰面崩裂,洪水裹挟着冰块涌上岸,半个村子都被淹了。
躲在土坡上的村民看着滔天浊浪,个个后怕不已,对着守拙连连作揖。九儿却指着河面说:“黄哥哥在水里推着冰块呢,不然水还要大。” 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,只见浪涛里仿佛有个黄色影子,正奋力抵挡着冰块,可那影子越来越淡,渐渐没入水中不见了。
开春后,官府要重修堤坝,知府亲自来勘察,见林家庄的土坡安然无恙,又听说了守拙预警的事,对他十分敬佩,想请他去县衙当差,掌管河工事务。守拙摆手道:“我就是个木匠,只会刨木头,不会管差事。” 知府又想请九儿去府学读书,九儿却指着作坊里的刨子说:“我要做能挡水的木头。”
没过几年,林老实无疾而终,临终前握着守拙的手说:“这辈子活得踏实,值了。” 守拙给父亲打了口柏木棺材,棺材上没刻龙雕凤,只简单凿了些榫卯图案,九儿在棺材盖内侧刻了一行小字:“大匠无言,护佑一方。”
守拙六十岁那年,把作坊交给九儿打理,自己带着王氏回了乡下老宅。九儿在黄河边修了座木楼,楼上摆着各种工具,楼下供着一尊黄衣少年的木雕,那木雕的眉眼,竟和当年黄九郎一模一样。有人说夜里路过木楼,能看见楼里亮着灯,还能听见刨木头的声音,夹杂着少年的说笑声。
赵敬文后来病死在破庙里,九儿让人把他葬在了后山,离黄九郎的坟不远。他说:“知错能改,就还是个人。”
又过了几十年,守拙和王氏也相继老去,九儿却还是中年模样。有天夜里,月光明亮,九儿把作坊交给徒弟,背着一个木匣子上了后山。人们第二天去看,木楼里的工具都不见了,只有那尊黄衣少年木雕还在,木雕前的香炉里,插着三支刚燃尽的香。
有人说看见九儿跟着一个灰袍道士走了,往西边去了,道士手里拿着个黄布包,九儿肩上的木匣子里,似乎有东西在发光。也有人说,在黄河边看见过一个黄衣少年和一个穿木匠服的汉子,正合力修补一处堤坝,那汉子的手法,和当年的林守拙一模一样。
如今林家庄的人还在说,每逢汛期,要是听见黄河里有刨木头的声音,就不用怕,那是守拙爷俩在护着堤坝呢。而镇上的老木匠们教徒弟时,总会说:“做活要学林守拙,做人要学黄九郎,心里装着别人,手里的活才稳当。”
发布于: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盈昌配资-配资合作-a股如何加杠杆-安全杠杆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